婚礼现场的水晶灯晃得人眼睛发疼。我站在红毯尽头,看着对面那个陌生男人,突然想起三个月前父母为这场婚礼四处借钱的模样。婚纱勒得我喘不过气,就像这二十五年被期待勒住的人生。当司仪宣布交换戒指时,我听见自己心底玻璃碎裂的声音。
红毯尽头的陌生人
两个月前的相亲饭局上,他谈论彩礼时像在菜市场讨价还价。婚房首付要我家出六成,说这是他们老家的规矩。当时我盯着他衬衫第三颗纽扣,数着上面细密的针脚,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两个家庭交易的筹码。

水晶杯坠落的慢镜头
香槟塔在尖叫声中轰然倒塌,我掀翻主桌时瓷盘碎裂的声音格外清脆。二十五年的乖乖女形象随着红酒渍一起泼在雪白桌布上,母亲晕倒前指甲掐进我手臂的痛感,竟比不过胸口炸开的畅快。
宾客们定格成滑稽的默剧演员,有人举着手机录像,有人张着嘴忘记合拢。我踩着满地玫瑰花瓣走向大门,婚纱拖尾扫过玻璃渣,像扫落前半生所有伪装。
出租屋里的第一缕光
三个月后的公寓朝东,每天清早阳光会准时爬上二手沙发的裂缝。我用婚礼预算付了两年租金,阳台上那盆绿萝是从旧家带来的唯一嫁妆。原来自由的味道是晒过的被单混着咖啡香,而不是喜宴上令人窒息的香水味。
上周末母亲突然来访,看见我素颜扎马尾的样子愣了很久。她临走前悄悄塞了张银行卡,说密码是我小时候学自行车摔断腿的日期。我们谁都没提那场夭折的婚礼,但阳台上两杯花茶升起的热气,模糊了彼此发红的眼眶。
婚纱改成的窗帘
裁缝店老板听说我要把婚纱改窗帘时,眼镜差点滑到鼻尖。现在阳光透过蕾丝帘子在地板上织出细密的光网,像某种温柔的封印。偶尔午夜梦回,还会听见婚礼现场的喧哗,但睁开眼看见月光里的窗帘影子,又安心沉入黑甜乡。
朋友问我后不后悔当众掀桌,我总笑着指指窗台。那里有盆从路边捡来的野花,在旧茶杯里活得恣意张扬。比起当婚礼上精致的提线木偶,我宁愿做暴雨后沾着泥点的向日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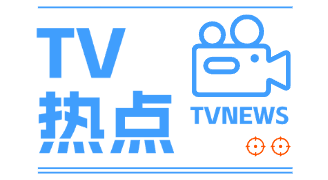





评论